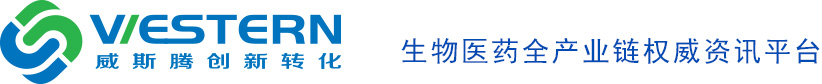在欧美人群多发的这种神秘消化疾病,最近也开始侵扰亚洲人群
炎症性肠病(IBD)的问题在亚洲日益增长,但这也代表着对其进行研究的黄金机遇。
“我连现在的病人都快顾不过来了,病例数量还在爆炸式上升。” 在胃肠病专家黃秀娟医生和同事的眼皮底下,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的胃肠病病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约七年前,黃秀娟医生开始在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接诊,当时,她遇到的主要是感染性疾病,比如肆虐胃肠道的肠结核病。但现在,病房里满是患有炎症性肠病(IBD)的青年男女。IBD 是一种终身性的胃肠疾病,如不治疗,会使人日渐衰弱。“我连现在的病人都快顾不过来了。” 黄医生说。“病例数量基本上是在爆发式增长。”

研究者认为,城市生活和食用方便食品可能是导致炎症性肠病 (IBD) 增加的两个因素。Tomohiro Ohsumi/Bloomberg/Getty
诊断:做好应对负担的准备
IBD 为世界各地的卫生保健体系都带来了挑战。IBD 很难诊断,治疗就更加困难了,而且 IBD 治疗(生物药物和手术)费用昂贵,药物治疗还需长期进行,医药费的负担往往会落在病人头上。在亚洲,所有迹象都表明 “(IBD)的流行度及其对卫生保健系统的影响将持续攀升,” 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的胃肠病学家黄秀娟说。韩国延世大学医学院的 Jae Hee Cheon 认为,“在未来 20-30 年,东亚的 IBD 发病率将达到与西方国家相同的水平”。
目前,帮助各国应对 IBD 造成的医疗和经济负担的工作正在开展之中,但亚洲的起点尤其较低。在伦敦结束研究并返回香港工作后不久,黄医生意识到,IBD 诊断不足主要源于相关意识的缺乏。“有些病人已经患病很久了,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那可能是 IBD,” 她说。
一般来说,像黄秀娟这样在西方受训然后又回到亚洲的医生可能是对 IBD 准备最充分的——他们在西方国家工作时接触到了大量 IBD 病人。以马来亚大学胃肠病学家 Ida Hilmi 为例,她从英国结束培训返回马来西亚后,受命主管该大学医学中心的 IBD 诊断与治疗工作。虽然 Hilmi 主要的工作是临床医生,但她仍然建立了一个 IBD 登记系统来追踪新的病例。
“这些病人中,大部分都将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那里的)医生或许很早以前在医学院上学时听说过 IBD,但却从未实际碰到过 IBD 病例。他们不会想到 IBD 的,”Hilmi 说。为了改变这一情况,她组织了一个 IBD 特殊兴趣小组,以增强卫生专业人员和病人对该疾病的意识,并在马来西亚各地的医院传播治疗策略。
但是,诊断 IBD 的技术挑战不应被低估。IBD 的许多症状都常见于其它胃肠疾病,如结直肠癌,医生需要首先排除其它潜在疾病才能得出确切诊断。诊断过程涉及验血、验粪、拍 X 光等检验方法,还有最重要的内窥镜检查。在亚洲,感染性疾病(如肠结核病)的存在使诊断变得更加复杂,它们表现出的症状几乎和 IBD 一模一样。医生一般会在病人得到确切诊断前先按其中一种疾病治疗,而两种疾病的治疗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这里有许多地方性传染病。如果有人得了腹泻,医生会开出多个疗程的抗生素,”Hilmi 说。
Cheon 表示,在韩国,IBD 诊断与治疗的复杂特性意味着大部分人都在高校附属医院接受治疗。黄秀娟说,随着财富的增加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们也更容易获得这一层级的医疗服务,因此,亚洲目前 IBD 发病率上升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诊断的改进。
她也有支持这一论断的数据。黄秀娟是亚太克罗恩病与结肠炎流行病学研究 (ACCESS) 的领导人,在过去 5 年里,该研究跟踪了亚洲和澳洲 13 个国家或地区的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IBD 的两种主要形式)新增病例。1985 年,香港的 IBD 发病率仅为百万分之一,2014 年则升至略高于百万分之三十。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 IBD 发病率明显更高,每百万人口中约有 200-300 人发病。事实上,在英国于 19 世纪中期报告首例 IBD 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IBD 一直被认为是欧洲人才有的疾病。但现在,随着全球各地纷纷出现 IBD 病例,人们的共识是任何人都有可能患上 IBD。“现在,IBD 确实是一种全球性疾病,” 麻省总医院克罗恩病和结肠炎中心的流行病学家和临床医生 Ashwin Ananthakrishnan 说。“如果只看病人数量,印度和中国可能还高于北美。”
病例持续激增为像黄秀娟这样的临床医生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机会。与其它免疫相关疾病(如多发性硬化症和牛皮癣)一样,IBD 发病率与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同步上升,但是人们对于驱动 IBD 发病的环境因素仍然所知不多。进入城市后,人们一方面能获得更好的健康护理和卫生条件,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在了更差的空气环境中。他们更有可能采取以室内为主的久坐生活方式,并且更有可能食用饱和脂肪含量高的方便食品。
已有研究将这些因素与 IBD 联系在一起,但是,确定有长期 IBD 发病历史的地区的病源仍非易事。黄秀娟说,要想理清 IBD 环境触发因素与遗传关联之间的复杂关系,理想的时机是城市化进程正在推进,而 IBD 发病率尚未触顶时。环境变化的程度可能与 IBD 的增加和特征相关,或可引出有关该疾病起因的新假设。“找出 IBD 起因的黄金时间是未来十年,” 黄秀娟说。
遗传学挑战
目前,人们已将 200 多个遗传变异与 IBD 关联起来。在首个覆盖欧洲、东亚、印度和伊朗等多个族群的 IBD 遗传关联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了 38 个与 IBD 相关的新位点(基因组区域),此前,人们已将其中 25 个位点与其它疾病或性状联系在一起,比如多发性硬化和胆固醇水平。
但亚洲的 IBD 增加并不是由新的基因突变驱动的——发生遗传变化所需的时间远远长于 IBD 在全球范围内爆发所用的时间。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遗传因素无助于理解亚洲 IBD 发病率上升的问题。Ananthakrishnan 说,遗传变异能帮助人们了解为什么环境变化对某些群体的影响大于另一些群体。例如,印度北部的旁遮普邦是亚洲溃疡性结肠炎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每年每 10 万人中约有 6 个新增病例。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印裔 IBD 发病率是马来西亚原住民的 6 倍,是华裔的 3 倍;显然,某种遗传风险因素发挥了作用。
在全球范围内,基因或变异带来的风险也有差异。例如,参与细胞自噬(一种细胞循环过程)的 ATG16L1 基因在白人中与患克罗恩病的风险有关,但并不影响亚洲人的 IBD 患病情况。NOD2 对于欧洲裔人群而言是一个风险基因,与侵袭性更强的 IBD 类型有关,但它在亚洲人群中却表现出了不同的 IBD 相关变异。更重要的是,在不同人群中,这些基因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 IBD 也有所不同。在亚洲,仅 3% 的 IBD 患者拥有同患此病的近亲,而在西方国家,该数字为 15%。
Ananthakrishnan 表示,除了整体风险外,特定的基因变异型可能也与特定的 IBD 外在表现形式相关。他的研究关注与 IBD 相关的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一个印度人生活在西方,那么他 / 她患上的克罗恩病的类型会更类似于在印度出现的病例,而不是在西方出现的病例。
JaeHee Cheon 在患有 IBD 的韩国人身上开展了遗传学、微生物组学和流行病学研究,他表示,来自不同群体的遗传和微生物数据也有助于为 IBD 患者定制治疗方法。Cheon 说,以研发中的微生物区系药丸为例,研究人员希望能利用这种药物将致病的肠道菌群替换为健康菌群,但它并不一定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所有患者,因为患者群体表现出的疾病特征以及他们对治疗的反应存在差别。
要在亚洲小国找到相关的遗传变异也并不容易,部分原因在于,IBD 仍然是一种相对罕见的疾病。举例来说,研究者认为马来西亚只有约 2000-3000 名 IBD 患者。这使得需要以数千病例为样本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几乎无法实现。Hilmi 表示,有鉴于此,研究人员可以退而求其次,选取一些在较大型的研究(比如西方的一些研究)中已经被识别为风险因素的基因变异,然后在较小的群组中测试它们是否会造成风险。
风险因素
“这是我们环境 - 影响领域的研究者都想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他说。但在当前,他只能提供一些笼统的建议:避免二手烟,早年间最大程度地减少抗生素使用,避免给子女服用非甾体抗炎药,因为它们会刺激肠道。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已经表明这些建议只是风险因素,而非经过证实的干预措施。要探究 IBD 背后的环境因素,研究者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关于环境在 IBD 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些最为清晰的证据来自移民研究。例如,针对加拿大安大略省居民的一项大型研究表明,南亚移民每年每百万人口中约新增 70 个 IBD 案例。虽然这远低于当地长住居民的年发病率——百万分之 240,但南亚移民子女的年发病率(百万分之六十 60)与长住居民子女的发病率(百万分之 72)几乎一样。
这项研究的领导人,加拿大东安大略省儿童医院研究所的儿科胃肠病学家 Eric Benchimol 表示,该研究最大的意外发现之一是,移民抵达加拿大时的年龄是 IBD 发病的强预测因素。移民时的年龄每增加 10 岁,IBD 风险就会下降将近 10%。这意味着,对于特定的遗传变异型而言,新环境中存在推高 IBD 风险的因素。
据研究人员推测,环境提高 IBD 风险的最有可能的方式是改变人体的肠道细菌。研究者的主要思路是,免疫系统和各种肠道细菌在童年期间逐渐发育成熟,因此,环境触发因素在这一时期影响较大。“这一发现十分激动人心,”Benchimol 说。美国和加拿大正在开展多项大型研究来验证这一理论。2015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炎症、抗生素的使用和饮食变化会独立改变克罗恩病患儿的肠道微生物平衡。使用消炎生物药物或饮食方法进行治疗似乎能让患儿的微生物区系成分恢复正常。
加拿大儿童 IBD 网络开展的 CIDsCaNN 研究正在收集新接受诊断的 IBD 患儿的数据,并对他们进行为期 18 个月的跟踪观察,包括南亚背景的儿童在内。研究人员正在收集患者的粪便样本,以探究微生物区系的组成,并记录有关早年环境风险因素的信息,了解触发疾病的原因。
多伦多大学的一支团队正在开展一项名为 “双子座”(GEMINI,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Exposures caused by Migration:Impact on Incidence of Inflammatory Disease) 的研究,旨在调查可能使健康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南亚移民患上 IBD 和其它自身免疫病(比如 I 型糖尿病和多发性硬化)的风险因素。加拿大是开展这些研究的理想地点,一部分原因是加拿大的国民健康登记记录让发现和追踪患病者十分便利,Benchimol 说。
机不可失
要理解导致 IBD 发病的环境因素,CIDsCaNN 等在一段时期内追踪患者情况的前瞻性研究是至关重要的。Ananthakrishnan 正在分析通过护士健康研究 (NHS, Nurses' Health Study) 收集到的数据,NHS 是一项长达几十年的纵向研究,其对象是 10 万多名在数十年间填写了病史和生活方式问卷的美国女性。
他发现,通过食用水果和蔬菜摄入大量纤维(每天约 24 克)的女性患克罗恩病的可能性比摄入量是她们一半的女性低 40%。其它研究发现,溃疡性结肠癌患者中也存在类似的倾向。另外,也有研究表明,高纤维摄入可以预防 IBD 患者旧病复发,IBD 动物模型支持纤维在减少 IBD 引发的炎症损伤方面所起的作用。整体而言,从高纤维饮食转向低纤维的西式饮食可能是导致 IBD 增加的部分原因,这种转变在亚洲城市尤其明显,Ananthakrishnan 说。
将西方研究(如 NHS)的发现应用于亚洲人群的一大局限是,这些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欧洲裔人群。虽然一些因素(如母乳哺育)可能具有普遍的保护作用,但是其它环境因素在不同族群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总是一样的。
举例来说,吸烟是西方群体患上克罗恩病的最大风险因素之一,但这却不适用于黄秀娟 ACCESS 项目的亚洲研究对象。ACCESS 数据似乎也表明,抗生素的使用对亚洲 IBD 患者具有保护作用,但在西方,它却被视为一项风险因素。要揭示亚洲人群抗生素使用与 IBD 的关系也更为困难,因为在一些亚洲国家或地区,人们可以直接购买抗生素,因此难以准确记录他们的使用情况。
若要从根本上了解亚洲 IBD 发病率上升的原因,需要在亚洲开展严格的研究。Ananthakrishnan 认为,从西方研究中收集到的数据集是理解环境风险因素如何影响慢性病的绝佳模型。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胃肠病学家和流行病学家 Gilaad Kaplan 说,研究人员可以综合采用这两类研究,以缩小暴露数据的范围,确定何时、以何种方式在亚洲的 IBD 研究中收集数据。
看着亚洲的 IBD 发病率节节攀升,研究 IBD 背后触发因素的黄金窗口也开始缩小,黄秀娟和她的合作者正在探索多种研究线路。她计划对比种族上相似,但生活环境明显不同的中国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比较内容从饮食选择到是否使用抽水马桶不一而足。
将目标锁定中国的 IBD 低发病率地区,比如浙江象山县和四川成都,或许有助于揭示可以保护某些个体免受 IBD 侵袭的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黄秀娟表示,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完成。“每天,我来到医院,看到转介来的新病例,就会问同事,‘这种病为什么会从天而降?它是从哪里来的?’” 研究人员明白,找出答案的最佳时机就是现在。
来源:Nature 自然科研
上一篇:情绪与肿瘤的密切关系,不可不知!